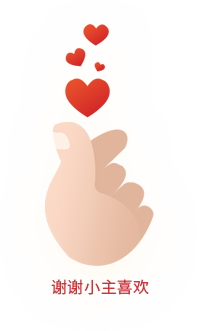网易震荡继续,新闻客户端掌舵人龙志离职,开始电商创业
2015年年末,网易门户最后一个重量级人物也选择离开。刺猬君独家获悉,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已提出离职。据了解,跟此前大多数网易离职者一样,他将选择创业,做跟女性相关的电商。南方系和网易系的背景,已经使得他受到多家风投的青睐。
网易新媒体中心是网易门户最重要的二级部门,负责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运营及创新。龙志的出走,标志着网易新媒体团队或将解散。
资料显示,龙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在读,有十多年的跨媒体平台管理经验。入职网易之前,曾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副主任,是南方系和中国调查记者代表性人物之一。
2012年,龙志加入网易,担任UGC中心总监,一年后,转任新媒体中心总监,正式掌舵网易新闻客户端,上任伊始,他力促网易新闻客户端ios及android两个运营团队的合并,全盘布局。自后,网易新闻客户端一路高歌猛进,用户从1亿多激增到3亿。
龙志及网易新闻客户端曾获十多个业界及学界奖项,他所带领的网易新媒体团队被认为是中国移动资讯领域最有竞争力和想象力的队伍之一。
网易新闻客户端旗下的网易真话频道是国内最早组建的移动端深度报道团队,推出了罗昌平《打铁记》等一系列经典报道。网易新媒体实验室制作的H5页面风靡一时,在业界引起重大反响。网易新闻客户端的王牌栏目 “轻松一刻”大胆探索转型。高举“有态度”的新闻理念同时,网易新闻客户端重构自媒体订阅平台,推动个性化资讯推荐。
龙志在资源整合方面亦有大手笔。他首倡的网易“英雄盛典”现固定为一年一度的网易“有态度”盛典。他主导的网易本地,从本已停滞的项目跃升为门户重点项目,今年更是单独拆分成本地事业部,成为2016年网易年度重点战略项目。
据网易内部人士称,11月11日,网易门户原副总编钭江明被宣布停职。前总编辑赵莹时代所有总编辑、副总编全离职。龙志在网易的上升空间巨大。但出人意料,龙志还是坚持离职。
本月初,网易门户内部邮件公示,一手打造了网易新闻客户端的移动互联网部总经理徐诗离职。这表明,龙志的离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分析人士称,徐诗与龙志的离职不是偶发事件。徐诗离职前,实际早已被架空,她所分管的业务都被肢解。而龙志及其团队也难展拳脚。
据了解,与此同时,在网易门户中销售变得越来越强势,销售介入产品内容越来越多,作为媒体出身的徐诗和龙志,均不愿意网易新闻客户端失去独立性。两人的先后出走也成为必然。
网易门户目前的核心竞争力是网易新闻客户端,据网易今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广告收入增长主要依赖网易新闻客户端。面对竞品的围堵和追赶,此时,龙志离职,对网易新闻客户端的后续发展可能是一个打击。
据网易新闻客户端内部人士称,多名主管业已提出离职,核心业务也被拆分,合并到PC端,网易新媒体中心面临解散。
前述知情人士称,除了高层,网易门户这一年中层流失更为严重,之前娱乐中心、新闻中心、时尚中心及体育中心等部门总监及主编成批离职,但对于更多的普通员工而言,不安全感很强,内部调岗转岗频繁。
2014年年底,网易门户运作上市,公司员工上下一气。岂料,2015年形势陡然生变,核心领导全部出走,年末人心惶惶。面对越来越多的离开,网易该怎么办?
附南方都市报深度部时期的龙志自述和喻尘眼中的龙志
他为南都、为公众奉献了2009年度最佳报道,他用勤勉、求真、准确践行着职业精神。在今天,他在路上,行走并记录;在未来,优秀报道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
《我似乎总跟自己过不去——南方报业2009年度记者龙志》
by 龙志
一
五年前的夏天接到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湘潭市政协空荡荡的大楼里采访,电话响起,我朝楼梯间走去,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编辑,你愿不愿意来南都?
对于一个已经工作两年的记者,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
如果一切如初,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在长沙总部的编辑正瞅着一个或者半个版面等着我填呢(当时是潇湘晨报驻湘潭记者,整个记者站就我一个人,当时的部门主管规定,无论有无版面,每天必须交一篇通讯主稿,两篇消息小稿)。我没有意识到,或将改变我的一生(或者说我从接电话后开始思索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我记得当时这样回答:我考虑考虑吧。
这里丝毫没有倨傲的意思,恰恰相反,在当时充满迷惑的语境中,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将要做什么。我所有的人生经验是:大二过后,因为某种东西破灭,赌气进了报社;一年后,又因为某些东西幻灭,赌气跳了槽。现在呢?问题又回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南下,到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城市?
几天前,我回过一次株洲,站在偌大旷荡的炎帝广场边上的株洲晚报6 楼,和当年的老同事们聊天。7 年前,我从这栋楼出发,踏上新闻的不归路。(这是我的幸运,以今日情境观之,又是我的不幸,和很多泥足深陷的记者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其它职业能勾起我的冲动)在这栋看起来外貌特征和生产的产品一样上了年纪的党报大楼里,总编辑居然决定录用一个大二学生,之后又送去北京培训,这是供职多年的老记者也争取不到的福利。至今聊起,很多老同事仍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短暂的接近两年的日子,是我最好的时光。在我入职前,报社新招了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80后年轻人,这些人构成了对党报陈腐体制的冲击,成为日后互相学习的参照和竞争动力。
就工作量而言,除了每月月底挂在通报栏上的考核排名关乎面子问题,只要你不在乎收入的差距,几乎没任何压力。因而身心上反倒自由。对于一个新手,最有效的途径不外乎模仿。黄河路边上有家席殊书屋,离报社大约10分钟路程,在那里,可以买到诸如《李普曼传》中文版,以及新周刊、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章。那里很快便成了这帮年轻人获取养分的阵地。
那时候的生活似乎还没脱离校园气息,上午睡到自然醒,中午联系采访,下午写稿,晚饭后打篮球、洗澡、讨论业务,到了11点左右去吃宵夜,午夜兜风,开着报社的破奥拓满大街呜呀呜呀的转,回到宿舍后,看书,睡觉。日复一日。
生活是一口老池子,风吹不皱,可以终老一生,但也阻挠不了年轻人很多想法在汩汩冒泡。
那时湖南本土媒体,以潇湘晨报迅猛崛起尤为侧目。深度新闻部在易伟掌舵时,也是最有冲劲的时候(比如《财经》欧阳洪亮,凤凰周刊前记者张志强,中国青年报湖南站站长洪克非当时均为旗下记者)。
有一天,我接到易伟的电话,喊去特稿部。第一次,考虑良久,觉得毕竟当年是破格录取,报社待我不薄,犹豫后拒绝了。那时候,我已经在晚报上每月试着写三、四篇整版的调查,稿子影响也有,报社也承认你,但每个月末考核表一出来,我的分数总是末尾一两位。到最后一个月,我连续4 篇稿子都在临签版时被撤换,这意味着,本月我将颗粒无收。领导可以纵容你、包庇你,但涉及到对体制的调整,则是铁板一块,因为他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易伟第二次邀请的时候,我便去了。
不幸的是,在我到晨报一周后,连易伟都去职到了凤凰周刊,整个深度部也不复存在。我流落到了湘潭。
这便是我当时的全部视野:起初,每天都盯着株洲,后来又守着湘潭。
听起过南方都市报,是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废止之后,媒体引来新一轮轰炸。我在转载的报纸上看过“陈峰、王雷”等人的名字,犹如现在有人看到过我的名字一样,很快便忘了。株洲火车站边上,也有个收容遣送站,也在这时候变成了救助站,我去采访过,外墙四周粉刷一新,亮锃锃的不锈钢大门,二楼屋内昏暗的墙上,还找到过几处血渍。
我丝毫不觉得会跟报纸上的这几个名字将有什么关联。因为夏日午后的一个电话,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起来。
二
我来南都后的第一篇稿子是《机枪手卿伯金的光荣与梦想》(原标题),多年后的一天晚上,跟已经任职网易的陆老师喝酒,还能背出文章的开头。
陆老师正是当年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人。2005年的南都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重新组建。我跟阿福是同一天同时报到的,见过方三文,在入职表上,我看到领导在他表格上写着:直接录用。而我的表格上则写着:试用期三个月。
我在做完第一单调查报道四川“猪链球菌”后,回广州,刚下飞机,接到陆老师的电话,通知正式转正,那是入职后的第20天。
一些牛人,比如喻尘子、王帅哥、贾叔叔一一拜过之后,深度人马也算凑齐了。姜大米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名字,微笑的大米,多有意思啊。那时候,我还有两年的光景可以称之为深度最年轻的记者,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跟我说,你们深度的人都宠你。
是啊,我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被宠坏。还好,不管名声在外还是藉藉无名,在陆老师看来,一切都要从文本开始学起。
于是有了人手一册的《普利策奖特稿卷》,通常是在白云仙馆、在苗圃,到后来最多的是513 办公室,每一篇稿子从结构到文本,从选题到立意,讲解得煞有介事,我们居然都能听得进去。
到两年后,文本在南都深度似乎走过了头,拐了弯,2007年宏城堡召开的年终会议上,“触及灵魂”的批斗中,我成了靶子。
我参与过最畅快的特刊采写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祭》,和喻尘子、姜大米、王吉吉以及帅帅的孙涛在唐山待了半个月,在后来大肆流行的媒体“特刊病”中,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这几年里,有两件事值得记录。一是2005年下半年,在洛溪桥脚几个黑帮里卧底近一个月,当初凭着“行侠仗义”的热情去做记者的想法,在日后竟成为我正视这份职业的伦理问题的源头。比如,我知道了黑帮买卖人口,却没有去举报,而是选择了所谓记录。比如,我通过隐瞒身份,感情投资,骗取别人的信任,到最后,当他完全信任了我,并在我面前完全袒露时,我却把这一切都呈现在报纸上。或许在别人眼里,这仅仅只是一种经历,随着稿子的刊发,眼睛又得看到另外的地方。
我似乎总跟自己过不去。脑容量的筛子网格特别小,对任何内疚的感情都过滤不了。久而久之,会沉积下来,直到不堪负荷。
第二件事是,我在2006年写了《彭水诗案》。这两件事,都给我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少赞誉,比如《工人房买卖劳动调查》获得了第一届南都新闻奖调查报道的银奖,《彭水诗案》获得了第二届南都新闻奖调查报道金奖、年度大奖。但我要提及的并不是这些名声,而是在做这些调查时,以及做完之后,沉淀下来的那些想法。对于《彭水诗案》的不虞之誉,则在我2009年做邓玉娇案所经历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三
2009年,是基于以上多年形成的惯性,不由得推着我走。调查记者干久了,越发觉得,工作和生活混淆,完全没有边界。这时候,你就等着,和女友的分手,对孩子的愧疚。还有就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老啦。
几年前,在去唐山的途中,飞机触地时颤巍巍的抖动,我紧张得要命,大米却淡定自若,她说,落地的瞬间,是她最安心的时候。她知道,目的地到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里,我住在员村一横路省高院后面,我几乎都是选择晚上回广州,城市喧嚣随夜色渐渐褪去;我坐大巴从机场到市区,从中山一立交下来时,总能看到“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到后来我搬到环市东路上,机场大巴的路线也变了,再也看不到这些霓虹灯,心里有些落空,总感觉缺失了什么。
当一个人有了归宿感,总归不是件好事。它意味着,你在老去,一度熟悉的人和事都可能是腐蚀你肌体的药剂,在你不复年轻的面孔下面,正在怠慢、消融的是你曾经斗志昂扬,现在理解并称之为的“梦想”东西。
现在,连我们部门都进了一个84年生的美女,这时刻警醒着我,不能再嫩或者老下去了。于是我又继续跑起来,狠命地跑,终于出了故障。
我又一次去了四川,去做地震一周年;“7.5 ”当天我去了乌鲁木齐,并且呆了20来天,我恨自己不能变成一架摄录机,而不是手中的笔、本子和傻瓜相机。我在想,如果我仅仅把它当成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苗人凤附体,从大漠打到雪山,从“鸡头”蹿到“鸡尾”,大可不必那么负累了吧?至少在外人眼里,还是个空中飞人呢。比如小乐的动力是爆米花的奶粉钱,兵哥的动力是下一次转山时最好能邂逅到女驴,我的动力呢?我既没有孩子,也不会持续地去想女人,我连这点乐子都没了,生活活该寡淡。
问题是,我又喜欢较真。于是我彻底悲哀起来,越发沉默,干脆钻到书纸里埋起来。2009年5 月我正在看一本书名叫《杀死一只反舌鸟》,在去巴东做“邓玉娇案”时,它是我行李箱里放着的两本书之一。
在书中,牛逼的哈伯。李笔下的律师父亲为了让天真的孩子理解成人世界里的偏见和冷漠,真相所包含的危机和无奈,贡献出了一句牛逼的话:
“呃,大部分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是对的,你是错的……”
“他们当然有权利那样认为,他们的观点也有权利受到完全尊重,”阿蒂克斯说,“但是在我能和别人过得去之前,我首先要和自己过得去。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
到后来,世人骂我,辱我,毁我,践我,恶我,我耳朵里听到的,眼里看到的,始终只有这句话。但这仅仅是权宜过渡,后来我明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做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心魔还在那里,在等着你某一刻不期而遇。等我明白过来时,已经种下祸根。
到10月底,写完《黑金帝国》,长年郁积的小罪恶终于突破极限,在海拔3650 多米的拉萨,病倒了。
喻尘眼中的龙志
喻尘(原南方都市报深度部主任)
与已经离开了南都深度、偏于一方为南都拓展疆土的贾云勇相比,他是平静的,甚至乏于故事性,几无可以显露的八卦传说;与在南都深度苦苦煎熬了 8 年,仍然在个人的叙述里尽显张扬的袁小兵比起来,他是他的延续,上面浅草一片,心中忧郁无限,可是,他注定不能延续他的现在和过去,因为出生于两个时代的浅草男人,自有他们各自光辉的一面;而与那位只小他一岁的海岛少年比较呢?一个心中有歌却很少唱出来,一个诗歌总与路途相伴,你看到他的诗歌时,就知道他窃窃的悲喜。
我以上说的那三个男人,都不会是他未来的模板,他有自己的道路,清晰可辨。这位叫龙志的青年,在走出湖南东南部他的故乡罗霄山后,前面的道路已经注定是999 条中最适合他的那一条了。虽然他在故乡的一所学校读了工艺美术专业,可是他不可能成为一位涂抹色彩的工艺师;比如他曾在鼎沸的歌厅投入K 歌,可以称得上是南都深度30余男女音律最准的一位,但他不能成为一位职业的歌手;他说,他曾痴迷于欧美电影大师的一场场杰作,可是他却没有真的去实践成为一位导演;其实,他还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比如你在他的文字里读到的他对故事解构的精到。
他在来到南都513 办公室之前,曾在长沙短暂停留,那只是他后来所有故事的预演,他之后个人的故事表明,他成了一位中国现实故事的编剧。
因为他遇到了这个堪称荒诞的时代和这个神奇的国度,真实的荒诞已超出虚构的故事,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小说家,每日都在发生的离奇故事已逼得小说家们智力低下。他必须在走到异于故乡的中国南方的这座城市后,寻找每一条通达这些故事的道路,他必须前去,聆听并叙述。
于是,他首先到达的是一处倒卖劳工的“工人房”,堪称完美的“卧底工人房”的报道,使这位当年不过23岁的记者进入到南都深度一批30余岁记者的视野。那一年,我和贾云勇、王雷、袁小兵、卢斌等中年记者开始注意这位新入伙的小弟。5 年以后,多位当年的中年兄弟已在他乡成就斐然,我等还在,年轻的小弟还在,虽然接连又有更年轻的同学入伙,可他,仍然是南都深度最年轻有为的一位,令我等年长者、他等年少者瞩目。
从23岁到28岁,于别人,是在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风月,或携春风在路,或醉卧酒肆,或踏歌而行。而于他呢,他经历了仅有的一次失恋打击,我曾怀疑过他后来满头的青春逝去与此有关,之后,似乎没有听说他恋爱第二次,直到今天。这是不是他从23岁到28岁成长的过程中最缺失的东西呢?不知是多了一份成长的烦恼,还是缺少一份烦恼。
他不得不将风月鲜少怪罪于一次又一次奔波在路上,那似乎就是他的恋爱,他的精神鸦片。从“彭水诗案”到“邓玉娇”,这是南都近年堪属在全国性重大事件得分最高的报道,从重庆东南部的边地小城到湖北野三关偏远小镇,他讲述的故事告诉了公众新闻事件的另一面,即最接近真实的一面。在“邓玉娇”事件最为喧嚣的那段时间里,他曾给我说他的压力,他的烦恼,作为年长的同业,我只能给他说:“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
他没有选择,他必须坚持,在国内同业一片浮躁,特别是与他同龄的同业中,踏实者更少的情境中,他没有选择的权力。最后,他坚持下来了,筋疲力竭,身心俱疲,“邓玉娇”一战耗掉了他前4 年储备的所有精力。但这是对的,我相信这种彻心彻肺的疲惫,终将化作未来成长的营养。
如果说到营养,他会指着头上的一片荒漠说,那里是多么的营养不良。于是,他总爱戴着一顶帽子,他好像在南都深度的第二年就与帽子成了朋友。我总有一个想法,掀起那顶帽子看一眼他被褪去的浅草,终有一次那顶帽子在一次酒席间混乱的传递中丢失了。帽子比他的下衣似乎还重要,他试图找回来,可席间的喧闹,在帽子经过一个高个子男人的头顶后,就在那个夜晚神秘消失了,至今谜底未解。
第二天醒来,他在那个下面坐着和他一样年纪同业的课堂上,展示象征着他的青葱的照片,他摸了摸尴尬的脑袋,那里写着一个囧。
我曾想告诉他,过去脑袋上的枝繁叶茂和今天的干枯烂草都不可以说明什么,那不是开始,也不是结局。我突然想起英国人麦克。莫波格在他一本书的扉页写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柑橘与柠檬啊》,你迟早要唱起它,勇敢前行……” 是的,你迟早要唱起它,而且戴着一顶帽子。
他迟早要唱起它,这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他在离开了故乡罗霄山之后,5 年之后,他所服务的南都深度已从当年8 、9 条枪壮大到今天的一片树林,多位年轻的兄弟都长成为大树了。我想给他说:“你看一下,自己不正是最枝繁叶茂的一棵么?”
是的,树叶子未能长在头顶,化作文字进入了骨头和血脉。兄弟,这是定数。
(作者当时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副主任)
江艺平点评
从小幻想独一无二的龙志,在独一无二的南都幻想成真。独一无二意味着,他和这张报纸注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成为新闻旷野的拓荒者。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ID:ctoutiao),给您更多好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