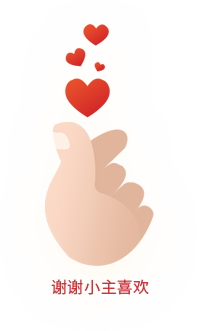城市住房政策失灵:巴西的历程及其启示
作者:邓宁华
来源:《社会保障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乡镇移民涌入城市,带来严重的住房问题,并要求国家进行住房政策干预。不过,国家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干预,既可能成功,也可能有“失灵”风险。以21世纪的今天的立场来看,在城市住房政策干预效果方面,欧美国家相对成功,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失败。特别地,拉美国家由于其“贫民区”和“非正规住房”现象,而被国内外研究者视为城市住房政策干预失灵的典型。拉美国家的住房政策为什么会和怎么样会失灵还很少有系统研究。大部分国内研究者都只关注拉美国家当前的状况与后果,而忽视其形成过程和历史根源;更一般地,大部分借鉴国外住房政策经验的研究,都关注已经发达国家的情形,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实际上,发达国家已处于后城市化时代,在政治和经济模式上与我国也不同,这样,其经验可能不一定适合于刚刚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中国;而对发展中国家状况及其比较借鉴的忽视,进而又使得正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所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贫民区”现象(表现为棚户区现象),以及“非正规住房”现象(表现为“小产权房”现象),难以得到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们的正视。此外,住房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取向泛滥,也导致比较历史社会学视角的缺乏,从而可能丧失对我国国内住房问题的整体的和历史的把握。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最大的拉美国家巴西为典型,对其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失灵的历史进程加以阐述,从而克服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有三个目的:第一,整体地和历史性地把握巴西城市化进程中住房问题、住房政策干预以及其失灵的具体状况;第二,揭示巴西城市住房政策失灵形成的根本的、历史的原因;第三,指出它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化”是本文研究的一个主线。巴西城市化从开始到完成长达上百年时间。这样,对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是研究开展的前提。参照城市化发展的S型规律,本文将巴西城市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阶段(1889-19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约14%),二是城市化水平相对较快的中期阶段(1921-1967年,城市化水平达到约50%),以及城市化水平相对缓慢的晚期阶段(1967-1991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5.95%)。按照上述三个阶段顺序,本文试图论证指出,虽然在城市化各阶段中巴西城市住房问题和住房政策干预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其在建国时即已确立并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三座大山”传统,却使其城市住房政策长期失灵,而住房问题则旷日持久。巴西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有重要参考价值。
早期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及其“三座大山”传统
葡萄牙殖民者16世纪建立了巴西,并在此后塑造了巴西的大土地所有制、种植园经济,以及其与宗主国间的依附关系。巴西1822年获得独立,并进一步形成了对“日不落帝国”英国和新兴强国美国的依赖。到19世纪末黑奴解放和封建帝国体制终结后,巴西的民主政治和国家自主性依然脆弱。在经济上,1890年代后,巴西的咖啡种植园经济甚至继续扩大,并且其收益被不断向巴西的经济与政治领域加以渗透和操纵的英国和美国所占有。这样,巴西从殖民时代开始、到建国时期、乃至1890年代后,对国外的经济与政治依附、政治上具有较强庇护色彩的封建主义传统,以及经济上对大土地所有制和种植园经济的依赖——本文称之为巴西的“三座大山”传统——的格局都一直存在,而这对巴西城市住房问题及其干预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城市化方面,巴西192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成年居民有1800万。其中,有独立收入的居民为900万人(其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为645.2万人),另900万没有职业或无固定职业。据此估算,全国劳动力的失业率高达50%,而其原因,则与大土地所有制与种植园经济下对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有关;而在这一年,如果将非农就业人口当成城市人口,那么,其城市化水平大约为14%。由上亦可见,巴西从早期城市化阶段一开始即面临着与大土地所有制和种植园经济相联系的工业化不足、充分就业不足和过度城市化问题。
住房问题及其后果
1888年5月奴隶制取消后,巴西大量黑奴逃离咖啡种植园,并涌入了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新政府将后者位于城市中心的别墅和庄园变成了学校和穷人的住房,但它们远远供不应求。
在政府乃至市场不能提供住房的情况下,大量缺乏充分就业的进城移民开始建设自建房,从而形成了贫民区。里约热内卢(1960年代前为巴西首都)19世纪末就在以前用于安置士兵和奴隶的区域内出现了第一个贫民区。随后,大量的移民工人开始在郊区空地上建立自己的自建房为主的贫民区,即“法维拉”。住户以码头日工、采石工人、建筑和市政服务工人、妓女等为主,住房黑暗、潮湿、拥挤程度突出,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缺乏。许多贫民区居民直接饮用河水,而污水也同时直接排入河中。在洗衣工所在的庭院周围,洗衣水排入了露天水沟中。
上述的贫民区问题带来严重后果。有官员认为:贫民区“这些地方的人完全缺乏道德感”,因为“拥挤在一起,肮脏的性滥交、骇人听闻的裸露,以及放荡的行为”随处可见。更为严重的是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后半叶霍乱蔓延到了巴西所有城市,共夺去15万人的生命。黄热病也在1850-1908年反复袭击并夺走6万人的生命;伤寒、疟疾、痢疾、肺结核也带来持续的威胁。与之相关,巴西人均寿命较低。1865-1895年包括巴西在内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出生儿童平均寿命没有超过27岁,而直到1930年也不超过36.1岁。
住房政策干预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问题,巴西国家精英在住房领域内采取了对乡城移民、国际移民以及工人阶级的分而治之的实践态度,并且只迎合少数阶级的利益。这一分裂性功能主义“潜规则”,使巴西居民缺乏充分的公民权利,并且构成了城市住房政策一开始即存在失灵的直接制度原因。
这一点可以由巴西这一时期的“住房卫生运动”来加以阐明。1889年10月18日,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更新建筑、兴建公共工程和消除传染性疾病。1902年新总统阿尔维斯和里约热内卢的咖啡利益相关者一起,试图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中心。从1902年晚期到1904年早期,里约热内卢市政工程取得巨大进展:在全市喷洒农药,拆除不卫生的建筑,拓宽道路,建设中央大道和各种各样的新的文化中心、旅馆、军事俱乐部、新日报办公室等。
然而,这些强制性的法令实施,没有照顾到普通城市居民的利益。一是不卫生住房的强制拆迁,使穷人被迫聚集在更不卫生的和疾病广播的区域;二是大多数外郊区贫民区居民长期以来要求建设人行道和主干道,但未得到理睬;三是内城区居民和店主也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前者找不到任何可替代的住房来源,而后者也缺乏合适的替代店面。上述的不满引起了社会反抗,甚至是武力性的对抗。针对武力对抗,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武力镇压。首先,在公共卫生上,1909年公共健康部门平静地向人群提供了接种服务,而没有遭受什么抵抗,之后天花就差不多消灭了。其次,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首都形成了有浓厚法国巴黎风格的、有开阔林荫大道和宽敞绿地的现代城市。再次,原来位于市中心的由小镇或贫民区占据的小山被清理,原居民变成了无家可归者,并被推到更远的边缘地带,而其规模则更为庞大。1890年里约热内卢市中心还占有52.7%的城市人口,1906年这一比重降低到了37.2%,1912年则进一步降低到了27.8%。相反,郊区和北部区域的人口比重,则从39.4%增长了到了64.5%。(12)最后,贫民区数量进一步增加。1880-1920年,里约热内卢共出现24个以自建房为主的法维拉。
总之,在早期城市化阶段,巴西即形成了政治上的封建主义、经济上对大土地所有制和种植园经济的依赖,以及对国外的工业经济的依附这一“三座大山”传统,并进而形成了工业化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与过度城市化等现象;而在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问题时,国家所采取的分裂性功能主义“潜规则”,则使城市住房政策一开始即存在失灵隐患。巴西早期城市化阶段的这一处境,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后来其城市住房问题及其干预的命运。
中期城市化阶段
随着城市化向中期阶段的迈进,“三座大山”这一巴西传统以及其分裂性功能主义规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城市住房政策失灵加重了城市贫民区问题。
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及其传统的再生产
在中期城市化阶段,国外对巴西的渗透和控制仍较突出,大土地所有制和对国外的经济与政治依赖依然严重,而国内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也缺乏成效。与上述情形相一致,巴西这一时期经历了混乱民主和军政府独裁之间的循环。1922年贝纳德斯就任总统后,采用限制言论自由、延长戒严状态、解散反对派组织等报复性的政策来维持公共秩序。1926年上任的路易斯总统取消戒严令和恢复出版自由。但1929年美国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却对巴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在军队支持下,1930年上台的瓦加斯总统开启了15年的军事独裁。在其任期内,巴西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却又不足以向源源不断的进城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到1945年,在军人的反对下,瓦加斯总统下台,从而终结了后帝国时代民主与军事独裁之间的第一次循环,而接任的仍是军人出身的总统。1951年后,瓦加斯重新担任总统,但却于1954年在家中自杀身亡。1961年,平民出身的夸德罗斯上台,不到7个月即辞职。他的辞职,使巴西脆弱的民主几乎再次崩溃。最终,从1964年,巴西开始走向第二次民主与军事独裁的循环。
当然,中期阶段巴西工业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在1966年前后达到50%这一城市化中期阶段的水平。但即使如此,巴西低度工业化和就业不足现象却仍然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1950-1970年间,巴西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增长了124%和142%,但城市人口却增长了208%。其中的原因,又与农村大土地所有制下的过高失业率有关。这一时期巴西农村失业率高达66%,迫使农村人口通过进城来解决失业问题,而后者又通过贫民区式的自建房来满足城市的住房需要。
贫民区扩张和住房政策干预
在中期城市化阶段,巴西贫民区和非正规住房继续维持并大量扩张,并带来各种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巴西城市化的迅速和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还在于新阶段下“三座大山”背景下的住房政策失灵。
首先,“规制工人”立法及其住房后果。1937年,瓦加斯政府规定,只有那些属于获得法律规定的职业的工人,才能并且必须加入工会,从而成为“受规制的工人”。不过,1940-1951年间,巴西的规制工人数量只有大约150万人,覆盖率很低,反映了它法律服务的严重短缺和根本性的政策失灵。并且,这一失灵在住房领域内也和分裂性功能主义规则一脉相承,从而加剧了住房政策失灵。在宏观方面,住房金融市场完全面向于中产阶级和规制工人。分期付款和商住两用公寓住房在瓦加斯时期兴起,并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和规制工人的美梦。但是,包括黑人在内的巴西非正规的移民工人则被排除在外,特别是在中心城市。在微观方面,巴西住房甚至也存在等级分裂。在所有的中上阶层公寓或住房中,都有前台的“社会”面和后台的“仆人”面,二者在电梯、进口、浴室等方面分开。对正规工人的住房供应也存在限制。1940年前巴西建立了应急性的公共住房供应,以应对1940年的租金上涨和社会抗议。这一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的,有很多缺陷,如规模很有限、社区成员的封闭性与单一性、自上而下的集权化设计、分配中的庇护主义以及远离市中心与缺少就业机会等。
其次,分裂性功能主义“潜规则”公开化及其住房后果。到1920年代晚期,里约热内卢市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不过,这一规划却使分裂性功能主义由“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因为根据这一政策,不同群体被分裂到不同的城市区域中,其中,上层阶级被置于南部,而郊区则用于安置进城移民和工人阶级。由于郊区更缺乏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应,并且更难得到国家的法律与行政支持,因此,住房非正规问题以公开的方式得以维持了。
再次,贫民区及其治理问题。这一阶段巴西政府在治理贫民区问题时,以拆迁为办法,未提供替代性住房供应,从而使问题更严重了。巴西贫民区大体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法维拉。它始于19世纪末的棚户安置区,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1950年里约热内卢约有20.3万法维拉居民,占城市人口的8.5%;1964年则上升到60万,达16%。二是非法分包。它始于1930年代郊区和远郊区废弃的柑橘园农地的分包。大量的乡城移民涌入、以60年代中期为典型的投机性住房建设、社会住房建设资金的缺乏等,推动了这一现象的大量蔓延。三是入侵。1950年代里约热内卢郊区已极其拥挤,只有环境很差和高风险的区域,如陡峻的山坡、红树林、河堤、沼泽地、山坡以及在高架桥、公园、道路上的剩余空地,没有被占据。但到60年代之后,这样的地方也开始陆续被填满。巴西贫民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特别落后。甚至到1970年前后,巴西城市仍只有50%有自来水系统,35%有污水处理系统;在圣保罗这一巴西最大的城市,只有55%的家户有排水系统、54%有自来水。贫民区居民或者要买自来水、或者还是要从池塘中或水沟中抽取。
最后,贫民区问题继续带来严重后果。在贫民区中,公卫生问题,正规就业不足问题,严重的失业、毒品、有组织犯罪以及警察力量的私人化等现象相互交织,并开始构成巴西社会的“癌症”现象。
总之,在中期城市化阶段,虽然巴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继续推进,但“三座大山”传统的再生产、分裂性功能主义规则的公开推行以及住房政策干预在保障公民住房权利上的失灵,则进一步造成了巴西城市社会与空间的宏观和微观分裂,加重了贫民区等城市住房问题。
晚期城市化阶段
在巴西晚期城市化阶段,“三座大山”阴影仍然未能根本消除,住房政策失灵现象依然存在,而以贫民区为代表的城市住房问题则旷日持久。
城市化的晚期阶段及其经济社会状况
吊诡的是,在巴西,军政府往往被认为是民主的“最后依靠”和解决任何困难问题的“终极武器”。1964-1985年是军政府执政时期,确实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1967-1973年的“经济奇迹”),但其大土地所有制、严重的腐败、裙带主义和国际的依赖与操纵却依然存在,而失业也较为突出。并且,巴西军政府也缺乏实现现代化的充分能力;1980年代军政府在国家经济治理上陷入一片混乱。而新接手的民主政府面对的又是一个烂摊子,而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造”。
在城市化上,在军政府领导的前期,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巴西城市化和乡城移民的迁入尤其迅速。据巴西的历来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巴西城市化水平已达到67.4%;到1985年城市化已经超过70%(约为71%),超出拉美平均水平。1991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5.95%;2000年和2010年则分别达到81.2%和84.36%。由于1985-1991年间城市化提升水平甚至要比前一个5年还高,本文将1967-1991年当成巴西的晚期城市化阶段。当然,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特别是80年代后)巴西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和非充分就业仍然很突出。
在晚期城市化阶段,即使巴西军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稳定和努力推动工业化,并也采取了以“全国住房银行”项目为主的全国性住房社会政策干预,但最终却还是失败了。
军政府“全国住房银行”项目
在军政府之前,巴西已经有了部分的公共住房建设和住房保障措施。但真正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却始于军政府时期的“全国住房银行”项目。
“全国住房银行”成立于1966年,其目的是自有住房,以“人人都有私人住房”为目标。目标是为了解决既有的800万住房赤字和每年新增5000套的问题。要克服住房短缺,全国住房银行所需要获得的投资基金高达GNP的6%,总投资估计达到了40亿美元。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有三个:(1)由雇主替员工支付的强制储蓄,它用于支持全国住房银行对社会住房的资助;(2)志愿支付储蓄,由SBPE机构(银行、建筑协会、储蓄协会)使用;(3)住房抵押贷款支付减免而产生的利润。
巴西全国住房银行项目包括四个发展阶段:
(1)1964-1967年是项目的培育和创建时期,包括建立这一机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老年保障津贴(1966年)和储蓄与贷款系统(1967年)。
(2)1967-1971年是业务转型时期。全国住房银行对面向高工资群体的项目实施优先资助;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得到重视。住房抵押贷款得以发展,并将资源转化到私人部门手中。债务和支付模式也得到了改变,建立了工资等价模式和工资变动补偿金。不过,由于各种问题,全国住房银行成了社会抨击的目标。
(3)1971-1978年是成为二线银行的时期。全国住房银行不再提供直接贷款,而是让私人机构来承担直接的运营责任。结果,其行动风格越来越像城市开发银行。另一方面,在住房方面,1973年“大众住房规划”项目试图将所有1~3倍最低工资者在10年内变成业主,并为此创造了1975年“场地与服务”项目,并为此而提供了减税刺激。
(4)1979年之后是重大变革时期。它成为穷人住房合法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法维拉升级、支持公司资助雇员的PROHEM项目、发展全国农村住房计划以及倾听服务对象的需求等。但因经济危机,这些变革并未达到目标。
“全国住房银行”的失败
通过全国住房银行系统,军政府在20年共建设了约500万套新住房,平均每年为40万套住房和公寓提供贷款。但巴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这一水平。因此,全国住房银行住房供应水平是远远不足的。实际上,联合国报告指出,1964-1986年间巴西75%的住房是通过自建房方式建造的。
在1980年代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全国住房银行的所有组成部分都遭受严重的危机。由于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工人提取了“储蓄与贷款系统”的储蓄,而抵押贷款持有人受损。菲格雷多政府错误的政策设计则使项目的系统危机在1984年前继续加深,并且最终失灵。
到军政府晚期,巴西贫民区数量反而激增了。在里约热内卢,1980-1990年新增的法维拉数量增加到105个,是有史以来增加数量最多的10年。1995年整个里约热内卢共有525个法维拉,时间最长的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再一次地,贫民区带来了数不胜数的暴力。1990年代末期巴西城市暴力犯罪达到警戒水平。它降低了城市中心的生活质量,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城市人口害怕公共场所;而私人保安则超出了警察力量。
1985年后,萨利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全国住房银行的遗留问题,即关闭全国住房银行这一头号公共住房系统支柱,而代之以新的执行计划。但效果很差,只完成了任务量的40%。在恶性通胀面前,政府变得无能为力。而在整个90年代,巴西住房政策可以视为对以前的住房政策失灵的反应。对通胀的恐惧、经济的不稳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政府的不尊重合同以及利益纠纷下房地产贷款合同的大量违约现象,使住房政策的重新启动面临重重问题。1985年后,拆迁和驱逐政策开始得到停止,以自建房和低标准住房为主的法维拉甚至得到鼓励。但在实践中,过高的登记费用限制了人们的正规化的努力;大量土地还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贫民区居民仍然被视为“二等市民”,而不被赋予城市基本设施和法律权利,并使之易于为政治力量所操纵;驱逐的阴影也还存在,如为举办2014年世界杯而进行的大规模拆迁工作。
总之,在1967-1991年间,乃至后城市化阶段,巴西“三座大山”传统仍然存在,住房社会政策干预对分裂性功能主义规则的运用还进一步发展,失灵依然严重。这样,到其城市化完成之时,非正规住房问题和贫民区问题还很严重。到21世纪初,巴西还缺少700万套住房。不过,巴西城市贫民区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36. 7%稳步下降到2007年的28%,虽然其根除却还有待时日。
城市化不能承受之重
城市化必然带来住房问题,并要求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的具体状况加以有针对性的干预。不过,国家自身却可能失灵。在巴西,从早期城市化阶段开始,非正规的自建房和贫民区等就是巴西城市人口满足住房需要的重要方式,而国家也采取了一定的住房政策干预行动,如早期城市化阶段的住房卫生政策,中期城市化阶段的城市规划政策,以及晚期城市化阶段的住房社会政策;不过,在每个阶段,这些政策总体上都是严重失灵的。直到今天,巴西城市贫民区和非正规住房都远未根除。巴西城市住房政策失灵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巴西建国之时已经确立、而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得到了再生产的“三座大山”传统。实际上,国外势力对国内的操纵、国内政治与经济精英(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对国外势力的依赖、国家精英构成的非现代性难免限制政府能力、造成政府失灵和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的不足,并进而抑制住房政策对强化贫民区和非正规住房现象的干预效果。特别地,本研究还表明,如果1889年取消奴隶制作为巴西城市化的开始,一直截止到今天(2012年),其住房政策失灵的时间,至少长达113年。这表明,“三座大山”这一历史因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巴西城市住房问题及其干预中的住房政策失灵,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情况。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城市化,结合巴西的个案研究结果,却也可以指出相关的启示。亦即,要避免总体性的住房政策失灵,谋求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是一个必要条件;加强法治和形成精英与大众间的利益共生格局,则是另一必要条件。中国在前一个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在后一个方面还不完全具备。以后,要加强法治建设、保障住房领域中的公民资格,并加强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和对经济发展果实的真正共享,才能根除城市住房政策失灵的深层根源;否则,现有城市住房问题,还将持续好几代人的时间。
本文来源:《社会保障研究》
注:本公众号转载文章仅用于分享,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后台联络授权或议定合作,我们会按照版权法规定第一时间为您妥善处理。
————————————
微信编辑:雨影晨新